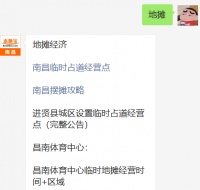现代犬儒主义者的恋物:斯拉沃热·齐泽克与信念动力学
作者:阿德里安·约翰斯顿
译者:祝杰
【译注】本文来自于2004年的《精神分析、文化与社会》,阿德里安·约翰斯顿博士是著名的斯拉沃热·齐泽克研究者,他所著的《齐泽克的本体论——一种先验唯物主义式的主体性理论》相当具备可读性。在进入正篇前,我首先要说明以下几点以便读者理解:①是原初犬儒主义(kynicism)与现代犬儒主义(cynicism)的区别,借用近期出版的《就这样,斯拉沃热,成了齐泽克》(2024,埃利兰·巴莱尔著,季广茂译,北京日报出版社)中的说法,一般而言,原初犬儒主义指古希腊犬儒学派第欧根尼的犬儒主义,即严肃认真的犬儒主义。它主张放弃一切私有财产,不再寻求欲望的满足,只需要一本书和一条狗,即可孑然一身、了无牵挂地行走天涯。现代犬儒主义则大不相同,它因为对社会感到厌倦,对制度感到绝望,所以主张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对一切都冷眼旁观,或者最多冷嘲热讽一番。稍后,齐泽克把犬儒主义与“犬儒化的当代主体”联系起来,说他们“一边在心理上拒斥意识形态,一边又在行为上追随意识形态”,却不造成所谓的“人格分裂”,因为在追随意识形态时“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②是我将fetishism译为了“恋物癖”以更贴合精神分析学和精神病理学的用法,但读者需谨记它与马克思所用“拜物教”一词是同义的;③我翻译本文的目的,主要是我看到了来自不少精神分析内部(包括布鲁斯·芬克)对斯拉沃热·齐泽克将源于个体临床的弗洛伊德-拉康元心理学运用到解析社会文化现象分析的批判,认为这是“非法操作”,但这种运用真的那么非法吗?可能由于此前对系统论的学习,让我对这种批判颇有怀疑,而约翰斯顿在本文中对该论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现代犬儒主义者的恋物:斯拉沃热·齐泽克与信念动力学
The Cynic’s Fetish:Slavoj Žižek and The Dynamics of Belief
摘要 斯拉沃热·齐泽克对当下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展开了批判性审视,并着重指出了“现代犬儒距离”这一现象,即个人虽有意识地宣称对现存体制不信服,但在行为上却“仿佛”真的接受了该体制的权威。齐泽克认为,在无意识中,这些现代犬儒主义主体即便公开表明无视意识形态,实际上却成为了这些意识形态的狂热拥趸。借助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齐泽克深入探究了现代犬儒主义、拒认和信念之间的结构关系,以此揭示了商品恋物癖和将自身无意识的信念归属于他者是怎样最终致使人们接受了对现状的默认。然而,齐泽克一方面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描述性-诊断性论述和其积极的规范性计划相互分离,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政治思想构建于拉康的“行动”概念之上,其思想本身就存在陷入现代犬儒距离陷阱的风险。
关键词 弗洛伊德;拉康;齐泽克;信念;现代犬儒主义;恋物癖
引言
人们或许很快就会想到针对斯拉沃热·齐泽克的常规方法论程序的一个反对意见,那就是他未经批判性思考,便假定弗洛伊德-拉康的元心理学与社会文化现象分析之间能够随意来回切换的操作是合法的。依据这种批评(可以说,这同样也能够轻易针对弗洛伊德本人提出),前者的概念体系起源于并且仅仅处理单一精神(the singular psyche)的运行,而后者则需要一套专门为应对集体结构而量身打造的不同理念组合。难道认为精神分析临床内部特有的方法能够轻松地输出到或者叠加在群体存在的公共领域不是一个问题吗?(见Nichol, 2001,p 152)。这种论点隐含着这样一种理念,即主体内部的动力学和主体之间的动力学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所以,齐泽克在忽略这条分界线这一方面是有着双重过错的,明显犯了一个荒诞的范畴错误:齐泽克路径的一个特点不只是运用精神分析概念来阐释文化实体(反之亦然),而且他还拒绝承认将拉康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等不同的知识流派结合起来有任何不妥。为何他不多留意一下那些能把精神与文化、局部与全球分隔开来的断裂呢?换言之,为何他把爱欲经济学/力比多经济学(libidinal economy)和政治经济学(political economy)看成是能够轻易相互替换的呢?【译注:力比多是弗洛伊德元心理学所假设的一种精神能量,精神装置的基本驱动力,也称“性力”,但其意涵远比单纯的“性”要更为复杂。我会在后文将libidinal economy暂译为“爱欲经济学”以跟“政治经济学”形成对应。】
正如齐泽克准确指出的那样,拉康竭尽全力地弱化——至少就精神分析而言——有时人们所认为的人类存在的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之间区别所具有的显著的清晰性与确定性。通常来讲,从拉康的视角出发,严格意义上的个体心理学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被精神分析仔细探究的独特个体,连同其丰富的记忆、身份认同、幻想以及行为模式,本质上都与更庞大、无所不包的中介矩阵相互交织。也就是说,个体始终超越了个体本身。同样,正如早期的弗洛伊德所坚持的那样,精神分析性诠释从来都不是将观念材料当作可分离的原子单位来处理——例如在他 1895 年的《科学心理学大纲》中,弗洛伊德宣称在构成心理层面的巨大精神内容网络里的每个特定节点本身就是一个“复合体/情结(complex)”,即多个联想元素的集合(SE,1:p327)——拉康也会坚决主张每个被分析的个体都是众多主体间关系(即与“小写 o”小他者[others]的联系)和超主体结构(即与“大写 O”大他者[Other]的联系)的集合。同样,拉康通过拓扑学中的图形——在当下的背景下,最好的例子是克莱因瓶,这是一种拓扑实体,其表面的连续曲率既促进又同时让识别独特内部空间的尝试变得混乱(Lacan,1964 - 1965,12/16164,1/6165)——难道不正是为了突出强调支持将个体心理学与社会文化分析分割开来的那些人所秉持的原始的内外二分法的无关紧要和不尽完备吗?
齐泽克运用拉康理论的这些不同面向,来为自己在面对被指责草率地模糊了个体与社会之间界限的情况进行辩护——“不存在原始的直接自体体验(self-experience),随后才接着是第二步,在符号秩序的运作中被‘物化(reified)’或者客体化(objectivized)。主体本身就是通过把其最内在的自体体验置换到‘物化’的符号秩序中才得以涌现的……没有最起码的‘物化’符号制度(symbolic institution)就不存在主体”(Žižek,2000a,p 27)。齐泽克在这里所做的不单单是回应针对他的指责:他通过争辩表明,不仅在对特殊心理和集体机构的分析之间摇摆是能够被接受的,而且任何坚持(不管是含蓄还是明确)纯粹个体主体性的有效现实、一种不受周围环境调节的心智(mind)的方法,都执着于一个浅显且毫无根据的神话,从而使那些提出此类指责的人处于守势。
然而,在齐泽克的观点中,劈开心理微观世界与城邦宏观世界之间阻碍的剑是一把双刃剑。他屡次否认,即便在拉康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教学里到处都能听到明显的结构主义转向,拉康也不能被理解成某种精神分析学领域的涂尔干或者列维-斯特劳斯。换句话说,齐泽克针对批评者的回应并非单纯地宣扬超主体性符号秩序的霸权,同时把心理主体的个性描述为大他者超越现实的附带现象残留。通过着重强调拉康宣称的“大他者不存在”(见Žižek,1992,p 58;1996,p 137;1999a,p 13;2000b,p 258;2002b,pp lxvii-lxix)的重要性,齐泽克做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行为,在拒绝对主体性和社会性做出稳定区分的同时,认为符号秩序的大他者只有在主体将其“仿佛(as if)”视为拥有稳定、独立的现实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调解系统时才会有效存在(尽管是以一种虚幻、短暂的方式)——“只有当主体如此对待它时,才有一个‘客观的’社会符号系统”(Žižek,2000a,p 26)。齐泽克继续说道,坚称:“拉康并非……涂尔干主义者:他反对对制度的任何物化,也就是说,他非常清楚制度仅仅是作为主体活动的执行效果而存在。只有当主体相信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行动层面(在他们的社会互动中)表现得仿佛(AS IF)他们相信制度时,制度才存在。”(Žižek,2000a,p 26)。可以说,大他者不过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关注主体和并不存在的大他者之间关系的“仿佛”这一维度,让齐泽克能够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极为具体的谜团之上。这个问题推动他采用了一种独特的办法,也就是在主体内和主体间的维度之间持续地并列以及跳跃:
......把原本用于个体治疗的观点拓展到集体实体的运用是否“合法”,并且举例来说,对于“现代犬儒主义者的恋物”这个例子,宗教是不是一种“集体强迫性神经症”?精神分析的重点完全不一样:社会,也就是社会实践和社会所秉持的信念(beliefs)领域,不但和个体经验处于不同的层面,而且是个体自身必须与之有所关联的事物,是个体自身必须体验为至少是“具体化(reified)”、外化的一种秩序。所以,问题并非“怎样从个体层面上升至社会层面”;问题在于:倘若主体想要维持其“健全(sanity)”、其“正常(normal)”的功能,那么制度化实践/信念的去中心化社会符号秩序应当怎样构建?应当在其中沉淀何种错觉,从而让个体能够保持理智?以大家都熟知的自我中心者(egotist)为例,他以现代犬儒的方式摒弃公共道德规范体系:通常情况下,这样的主体只有在这个体系“存在于那里”、获得公众认可的时候才能够发挥作用——也就是说,为了在私下里成为现代犬儒主义者,他必须假定存在“真正相信”的天真的其他人。(Žižek,2002b,p lxxii)
齐泽克在其他地方同样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阐释了他有关意识形态分析的核心理论关注点(Žižek,2001d, pp 113-114)。以这般精准的方式构建心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他针对那些时常抗议元心理学理论不适宜用来解释文化、政治和经济现象的同一批人对精神分析的批评,提供了一种优雅的回应。倘若集体的、社会符号的大他者凭借其主体与其互动的模式而成为当前的样子,“仿佛”它是一个独立且自主的秩序,那么忽略作为塑造主体性的驱力和欲望领域的爱欲经济学,就等同于忽略社会政治经济学本身的根基(作为制度化的大他者[grand Autre])。正如从拉康的视角来看,心理的内在性被塑造为与超主体性矩阵(trans-subjective matrix)的“外部空间”连续的曲率一样,所以,依照齐泽克的说法,在反思反转(inverting reflection)的时刻,这种更为宽泛的外在性也必须从理论上被视作一个其轮廓由其组成元素决定的空间。个体微观世界与集体宏观世界之间部分与整体关系的相互性是毋庸置疑的。对于齐泽克而言,“不存在没有外在的内在”,相应地,“也不存在没有内在的外在”(Žižek,2001b,p 55):
……对精神分析的标准“进步性”批评……是借助无意识的力比多情结(libidinal complex),甚至直接提及“死亡驱力”来对痛苦和心理苦难进行精神分析性解释,致使破坏性的真正原因变得难以察觉……我们获取的并非对外部、实际社会状况的具体剖析……因此,我们得到的是未解决的力比多僵局的情形;不是对导致战争的社会状况的分析,我们得到的是“死亡驱力”;不是社会关系的转变,而是在内在心理变化中寻求解决办法,在“成熟”中寻求解决办法,这应当使我们能够接纳现实的社会状况。从这个角度来讲,对社会变革的这种追求本身被指责为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难道这种通过对社会权威的“非理性(irrational)”阻抗来展现其未解决的心理紧张的反叛者的概念,不正是最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吗?然而……这种将原因外化到“社会状况”中的做法同样是不正确的,因为它让主体避免直面自己真实的欲望。借由这种对原因的外化,主体不再参与自身所经历的事情;他对创伤持有一种单纯的外在关系:创伤事件不但没有激发他未被承认的欲望核心,反而从外部打破了他的平衡。(Žižek,1999b, pp 59-60)
拉康派精神分析在社会性方面能够提出并回答的关键问题于是就变成了:主体必须怎样去构想其周边的集体环境,才能够接受并遵循其约束?(见Žižek,2001d,pp 113-114)。在进一步展开探讨以前,有一个简短的警示说明是必不可少的。人们或许会产生这样的一种印象,即前面对于主体-大他者(非[non-])关系的拉康-齐泽克路径的描述,意味着随性地、毫无条件地舍弃了一方面是个体的微观世界,另一方面是周边的社会文化宏观世界之间的所有层次差别。但所提出的主张其实更适度一些,也没那么具有争议性:具体来讲,就精神分析来说,这种层次差别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suspended]”或者“括起来[bracketed]”了,因为它们和分析调查以及诠释没有关系(尽管在精神分析的领域之外,这些层次差别并非被认为是站不住脚或者不存在的——只是这不属于恰当的精神分析解释范畴/管辖范围)。也就是说,分析侧重于外化、客体化的符号秩序作为一种具体化的整体呈现给必须“同意”受其支配从而成为与该秩序相关的那种主体的方式。当应用到意识形态等现象时,弗洛伊德-拉康理论并非直接以相同的方式关注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学等领域有关的对象。这些学科针对意识形态的探究通常试图解决这种跨个体的社会符号系统本身,而分析则提供了不同且额外的东西,也就是洞察个体怎样构建关于他们自身所处其中的这个系统的“幻想”,这些幻想让他们能够参与其中(不管是真诚还是不真诚,见Kay,2003,p135)。为了阐述一个完备且有力的意识形态理论,需要对硬币的两面进行描述。
第一部分:诊断——恋物癖与对信念的拒认
在其整个思想发展进程中,齐泽克多次着重强调“现代犬儒距离(cynical distance)”的关键意义。这是一种带有困惑或者嘲讽意味的不相信态度,对于意识形态的有效运转而言(Žižek,1989,p33; 1992,p x;1996 ,pp 200-201;2002b,p251)。主体默认一套规则、规范和惯例(即一个大他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能够维持起码的健全自我或者个性意识,也就是把自身设想为怀疑论者,不太情愿地在一群头脑简单、容易受骗的信徒中“随大流”,换句话说,在那些替他们持有信念的“假设相信的主体(subjects supposed to believe)”之中——“个体将自身的信念转移至大他者(体现在集体中),因此大他者代替他们去相信——个体作为个体则保持健全,与官方话语的‘大他者’保持距离”(Žižek,2002b,p lxx)。在阐释“意识形态在当下似乎是怎样运作的”时,齐泽克指出,“我们表演(perform)自身的符号性使命,却并不承担它们,也不‘认真对待它们’”(Žižek,2002c,p 70)。在齐泽克的描述当中,玩这种下意识自欺欺人的现代犬儒游戏——这种现代犬儒主义使得对社会符号权威实际上的恭敬服从在心理层面能够忍受——的主体,持有了和奥克塔夫·曼诺尼(拉康的一位分析家兼学生)所描绘的恋物癖者相同的看法:“我心里很清楚,但尽管如此......”(Mannoni,1969,pp 12-13,32)。当下的资产阶级商品恋物癖者,自认为自己是开明但厌倦的现实主义实用主义者,步入了一个头脑冷静的“后意识形态”时期,却极力忽略他们的立场本身完全被意识形态所充斥这一事实(Žižek, 1999b,p68;Kay,2003,pp 134-135,151)。
在现代,现代犬儒主义者实则是最为狂热的忠实信徒。他们借助一系列精妙的投射与外化手段,对自己所钟爱的虚构事物坚定不移。需要指出的是,在齐泽克看来,信念并非一种内在的、以第一人称表述的心理属性或者心智状态,而是一种具有浮动特点、可传递的功能,能够存在多种形式的置换(displacement)(Žižek,1997,pp 106,108)。晚期资本主义的现代犬儒主义者在言语和实际社会行为表现方面存在差距,这表明“现代主体虽然明确宣称不相信,但在其无意识(幻想)中却深信不疑”(Žižek,2002b,p cii)。在时髦且时尚的后现代那种对“体制(The System)”(或者用流行俚语来讲,“那个人[The Man]”)表示不相信的故作姿态背后,隐藏着康德在其 1784 年的文章《什么是启蒙?》当中所阐述的现代性的权威论断:“你尽可以就你所想争辩的进行争辩,但是要服从!”(Kant,1983, pp 45-46)。当前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所采取的策略,就是鼓励个人尽可能地表示不屑(dismissive),如此一来,他们就能将自己的顺从视作非个人化、非自身所有的东西,进而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从来没有人会把自己展现为一个顺从者;当下,每个人都是反顺从者,不管外在表现怎样,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个体。在这样充满反顺从的环境氛围之中,社会生产机制居然还能够在哪怕是极其微小的程度上发挥作用,这着实令人感到惊讶。
齐泽克本人在针对信念于意识形态方面所发挥作用的各类解释里,清晰地运用了恋物癖的精神分析概念——这一运用因如下事实而得以增强:马克思将“商品拜物教/商品恋物癖(commodity fetishism)”称作资本主义的典型特性(Marx,1906,pp 81-82,83),另外,拉康认为是马克思发明了症状(symptom)的分析性概念(Lacan,1971, 1/20/71 ; 1971-1972 , 1/19/72)。尽管弗洛伊德在其 1927 年有关该主题的论文中,把他最为著名的关于恋物癖的探讨局限在其于维持对阉割事实的“拒认(disavowal)”(Verleugnung)里所起到的作用(Laplanche and Pontalis,1973,pp 118——在这篇论文中,恋物(通常是一个不显眼的日常物品,被恋物者赋予了超常的力比多投注)被界定为缺失的母性阳具的替代品(SE 21,p 152-153)——这种心理防御机制的影响或许远远超出了性方面的问题。确切来说,弗洛伊德式的恋物癖者并未压抑他们所防御的不愉快念头;并不是某些痛苦的心理内容被转移到了心灵黑暗、难以触及的角落。相反,通过拒认的过程,恋物癖者成功地否认了在其感知或智力意识领域内出现的特定特征。然而,这种独特的防御策略只有凭借同时进行的、平行的恋物化过程才能够实现:对弗洛伊德而言,现实中明显的缺失,一种恋物癖徒无法接受的缺失,被一个外部实体(即恋物对象)所遮掩,该实体被提升到与被否认的原始缺失(即母亲不存在的阳具,SE 21,p 154)相同的力比多地位。只有通过这种恋物假体,允许避免承认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恋物癖者才能(无意识地)维持他/她的“仿佛”态度”——若剥夺恋物癖者的恋物,那拒认作为一种有效的防御(也许伴随着恋物癖者自身的现实感)就会彻底崩溃。
齐泽克断言,超脱的现代犬儒主义乃是当今后现代、晚期资本主义主体的典型态度。与此同时,他还指明,恋物癖近乎是一种普遍的“病态”,这类似于弗洛伊德在论及“文化神经症”时所描述的(SE13;pp186-187;21;pp 43-44)。效仿弗洛伊德,齐泽克严格区分了压抑和恋物(fetishization),认为二者是心理所采用的两种不同防御机制。在压抑当中,主体会阻止创伤性记忆或者不愉快的观念内容进入其认知的受限领域。压抑的相关产物是“症状”,即个人经验领域和/或行为模式中一个显著却看似毫无意义的特征,这是因为被压抑的材料对主体的现实生活造成了扭曲影响。由于压抑的审查作用,有意识的个体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意识到症状作为被压抑内容的病理性回归的意义与功能。而另一方面,恋物癖者则是有意并且明知地“享受他们的症状”(Žižek, 2001b,p 166;2001c,pp 13-14)。
此外,齐泽克宣称,恋物癖者通过牢牢抓住某个被赋予过度、不成比例重要性的物品,在他人面前所展现出来的形象,并非是沉浸于其独特幻想云端的妄想性倒错者(delusional pervert),而是一位坚定、务实的现实主义者。恋物癖者,不管是凭借坚忍还是讽刺,都能够承受日常生活的严酷与艰难——“恋物癖者并非迷失在个人世界里的梦想家,他们完完全全是‘现实主义者’,能够接纳事物实际的模样——因为他们拥有能够紧紧抓住的恋物,以此来抵消现实的全部影响”(SE13 ; pp186-187 ; 21 ; pp 43-44)。然而,倘若从恋物癖者那里拿走恋物对象,这种玩世不恭、务实屈从的伪装就会崩塌,致使主体陷入抑郁、绝望甚至精神错乱(换种说法,失去恋物的恋物癖者,会经历拉康所说的“主体性贫困(subjective destitution)”;见Žižek,2001c,p 14)。所有这一切带来的结果是,针对当今资本主义城邦居民中普遍存在的玩世不恭的屈从和悲观现实主义的明显、时髦态度,提出了一条特定的怀疑诠释学准则——“所以,当我们被这样的言论所轰炸,即在我们这个后意识形态的玩世不恭时代,没有人相信所宣称的理想,当我们碰到一个声称自己不再有任何信念、接受社会现实本来面貌的人时,我们应当总是用这样一个问题来反驳这些言论:好吧,但是让你(假装)接受现实‘本来面目’的恋物在何处?”(Žižek,2001c,p 15)。自然,齐泽克提醒读者,马克思本人早就理解了货币和商品本质上的恋物/拜物性质(马克思对这些实体的描述提及了“魔法”“神秘化”和“变态/倒错”,指的是在社会经济交换过程中流通的物品形式所凝聚的病态幻想对物质现实实际状况的模糊;见Marx,1906,pp 81,105;1967b,pp 826-827)。这意味着,要是当今晚期资本主义主体的微薄薪水和各种小科技玩意儿被拿走,他们对现状的现实接受的伪装会即刻消失(Žižek,1999b,p 68)。在齐泽克所描绘的当代世界中,恋物癖并非一种异常、越界的现象,而是社会现实中几乎与生俱来的结构特点,是统治意识形态主体的一种必要应对技巧。
尽管人们或许有着清晰的印象,认为这些概念是专属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的,然而齐泽克却提及,涉及现代犬儒主义、恋物癖以及信念置换(the displacement of belief)的动力学属于一种非历史性的必然,是人类状况普遍存在的特征——“‘假设相信的主体’这一现象是……普遍的和结构上必需的”(Žižek,1997,p106)。接着,他进一步指出,“通过一种恋物癖,主体‘借由他者来相信’”(Žižek,1997,p 120)。所以,恋物癖和“假设相信的主体”是所有人和任何情境下的现实中原本就存在的。从这个层面来看,齐泽克为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成功地将自身推销为唯一可行的社会经济选择这一问题找到了答案。正如齐泽克本人所言,当代的政治想象力已经抵达了一个令人衰弱的封闭节点;除非内部经济发生内爆或者外部强加的灾难(不管是自然引发的还是“恐怖”造成的)导致灾难性的崩溃,否则在社会想象当中,资本主义似乎成为了新的“千年帝国”,能够在没有任何偶然的创伤性干扰的情况下一直延续下去。因此,有关当代政治的主要集体幻想最终以“资本主义或一无所有”的被迫抉择而收场:要么是资本主义、自由民主意识形态的积极社会经济规划,要么是无政府主义、世界末日般的完全不存在任何制度的消极选择(而并非,例如,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等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愿景之间做出选择)。根据这种普遍的心理状态,资本主义也许很糟糕,但它却是唯一可行的选项(Žižek,1999b,p 55;2000c,p 10)。人们难免会在拉康研讨班十九的标题“……或更糟”中听到这种困境的回响(见Žižek,1989,p 18;1996,p 4;1997,p 105,120;2001b,p16)。这同样让人回想起温斯顿·丘吉尔有关民主的评论(在 1947 年 11 月 11 日对英国下议院的演讲中)——“没有人会佯言民主是尽善尽美或无所不能的。事实上,曾有人宣称,民主乃是最为糟糕的一种政府形式,只不过是其他所有形式都已在不同的时期被尝试过罢了。”
齐泽克将金钱挑选出来,把它当作资本主义恋物对象的典型(Žižek, 1989,p 18;1996,p 4;1997,p 105,120;2001b,p 166),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三卷里也多次提及这一点。在马克思的看法中,金钱无非就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商品,它已被抬高成为所有其他可能商品的替代品(见Marx, 1906,pp 98-99,155;1967a,p 28;1973,pp 213-214),充当着“卓越的商品(the commodity par excellence)”(Marx,1967b,p516)——顺便说一下,拉康对于崇高化/升华(sublimation)的定义,即“一个对象被抬高到原质(the Thing)的高位”(Lacan,1992,p 112)的这种运动,跟这些相同的马克思主义公式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通过着重强调金钱作为典型恋物对象的地位,还有他有关恋物现象无处不在的精神分析论断,作为人类能够承受现实的一个特点,齐泽克(不经意间)展现出了为什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或许确实,至少在暂时的情况下,有效地战胜了它的竞争对手。它通过在一方面是主体性欲望的逻辑,另一方面是商品的社会生产和流通之间达成可能是迄今为止最完美的寄生融合而获得了这一胜利。假如像齐泽克所宣称的那样,恋物现象是某种不变的必然存在,那么资本主义通过把它的运作存在建立在作为普遍恋物货币的金钱之上,作为一种恋物的“最小公分母”发挥作用,这是一个空洞的、形式上的变量,能够替换在市场交换网络中流通的其他特殊恋物对象的各种不同内容,成功地利用了每个主体坚持某种“恋物”作为使现实能够忍受的实体的需求。所以,齐泽克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基本论点提供了一种补充的精神分析转向,即作为经济活动领域的“市民社会”最稳定的化身,是特定主体的自私性(无意识地)服务于更大的集体整体的那种(Hegel,1967,pp 124-125,129-130)。在齐泽克的这番论述当中,资本主义不但通过自身理性的狡诈,把个体私利的蛮横力量当作维持其总体经济基础设施的手段来强化自身(依照黑格尔的论点),而且向每个人宣扬通过通用的金钱媒介获取他们所需的任何珍贵小物件的可能性,不管他们是愉快地还是现代犬儒主义地默认现状。然而,金钱是不够的;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由于货币形式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制度比资本主义早了很多年,所以肯定有其他的东西要为资本主义对人类欲望的特别有效的利用负责。
通过着重强调主体与大他者、个体心理与集体城邦的共同构成,齐泽克让自己摆脱了一系列的问题(也就是有关将精神分析和社会政治理论并列是否有效的批评),但却又制造出了另外一系列令人望而生畏的难题。倘若正如齐泽克所坚决主张的那样,爱欲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始终已经相互交织,那么弗洛伊德-拉康的驱力和/或者欲望理论对于理解社会政治问题会有怎样的增益呢?这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很有可能促使齐泽克在强化其马克思主义言辞的同时,愉快地接纳犹太-基督教的神学主题。这种宗教转向在他的文本当中出现,大概跟他开始自称是斯大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时间差不多。鉴于齐泽克(并非有意)承认精神分析或许的确非常清晰地表明,资本主义在把人类欲望当作自身延续的工具这一方面极其有效,这种基督教与强烈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的完全违反直觉的结合或许能够变得更容易理解。
在研讨班十六当中关于马克思的一次简短跑题里,拉康暗示了一个如今大家都熟悉的观察,即在晚期资本主义里,使用价值不再主导商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确实是有用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但它所做的那些事情是无用的……这正是它的问题所在”(Lacan,1968-1969,3/19/69)。 齐泽克基于此进一步阐述,指出资本主义对多余需求(superfluous wants)的人为制造跟拉康有关人类欲望核心存在根本的、无法满足的缺失这一论点存在关联:
这就是资本主义“消费”的爱欲经济学所在:这些物品/对象(objects)不仅满足或满足了已经给定的需要,而且创造了他们声称要满足的需要(宣传通常以这样一种方式运作,即消费者“意识到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的欲望”),最终扭曲了马克思的旧观点,即生产创造了消费的需要,为对象的生产创造了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对象不再……局限于“自然”的口唇客体、肛门客体、声音、凝视和阳具,而是涵盖了不断急剧增加的众多文化性的崇高化,然而,这跟某种缺失紧密相关——资本主义消费的过度总是作为对根本缺失的回应而发挥作用。(Žižek,2001c,p 21)
在同一本书的其他位置,齐泽克提及了“欲望的先验幻觉”(Žižek,2001c,p 68)以及“欲望本身所形成的内在、固有的阻碍”(Žižek,2001c,p 76)。这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把精神分析融入马克思主义的尝试存在很大差异:举例来说,马尔库塞把个体爱欲经济学的功能失调主要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无端特性,类似于一组暂时并且并非必要的特定社会经济安排(Marcuse,1955, pp 137-138,139),然而齐泽克在依靠拉康的情形下,更倾向于认为这种功能失调是天生的且不具有历史性的观点(Harpham,2003, p 462)。
依据拉康的爱欲经济学理念,主体能够承受欲望带来快感的缘由在于,它们往往是以局部且不完整的形态呈现,并映衬于“更多的东西(something more)”这一背景之中(也就是拉康所讲的“剩余享乐[surplus jouissance]”,如同更多有待来临的享乐那不断后退的地平线;参见Lacan,1998,pp 111-112;2002,p305,309)。另一方面,倘若个体有意识地抵达了绝对、完整以及充分享受的境地,他/她就会遭受创伤甚至被摧毁。齐泽克本人证实了资本主义消费正是以此种方式运转的。作为一个纯粹的数量实体,人们总是能够拥有更多的钱:拉康所认定的有关“大他者原乐(jouissance of the Other)”的幻想的资本主义版本,就是倾向于持续地将自身的财富与总是更为富有的他人的财富进行对比。同样,多余消费品的增加以及各种产品精心规划的技术过时,确保了人们总是有更多的东西有待获取,总是缺少这样或者那样的东西——在市场这个大他者当中并且由其不断填补个体的缺失。从拉康的立场出发,资本主义的部分力量(特别是其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在于,在由一系列广泛传播的幻想所支撑的集体系统层面上,巧妙地效仿了在单个主体的心理构成层面上运行的逻辑。所以,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形容为“吸血鬼”的形象是极其恰当的(Marx,1906,p 257)。因此,齐泽克的基督教转向跟他一些听起来奇特的提及斯大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的出现相互吻合,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借用已故海德格尔的话语,“现在只有革命的上帝才能拯救我们”)。简而言之,想要战胜这样一个狡黠且强大的对手,似乎非得借助奇迹般的神之干预才行。
因此,齐泽克常常因其貌似激进马克思主义,实则为隐藏在虚张声势面具背后的隐秘保守派这一身份而受到批评。朱迪思·巴特勒把这归咎于他的拉康主义,觉得拉康的非历史先验论(比如,他将符号意义上的“被阉割”的欲望和“实在界的基石”描绘成人类爱欲本质里永恒不变的特征)致使任何接纳此观点的人,都悲观地嘲讽全面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变革的前景。她指责齐泽克成为拉康表面上过早且不合理地把历史调解现象的短暂方面视为主体性的普遍且必要组成部分的牺牲品。所以,巴特勒暗示,鉴于拉康显然要对各种仓促的具体化负责,齐泽克难以想象某些变革的可能性(Butler, 1993, pp195-196, 198-199, 206; 2000, pp152-153)。同样地,彼得·迪斯坚决主张,不管齐泽克如何慷慨激昂地抗议,齐泽克潜在的哲学信念让他不可避免地倾向于保守主义(Dews,1995, p 252;1999,p22)。
齐泽克在回应此类攻击时,态度似乎有些摇摆不定。他早期的作品主张把拉康解读成某种先验哲学家(Žižek,1993, p 3)。然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他却觉得这一立场难以成立从而予以否定(Žižek,1999c,pp 276-277),尽管像“先验的”和“内在的”这类内涵丰富的术语在他近期的著作里还是时有出现。他就改变想法所给出的原因之一是,正如他所讲,“先验化”拉康就等同于“对失败的庆祝”(Žižek,2002b,p xii)。这也就是说,将拉康有关爱欲经济学的理论的某些方面提升至影响任何可能的人类现实的普遍先验条件的地位,很有可能滋生一种听天由命的保守主义,要么觉得任何从根本上“革命性”的方式都无法真正改变任何事物,要么觉得尝试也毫无意义,因为反正人们注定要过不满足的生活。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齐泽克对巴特勒等批评家的让步显得过多了,如此一来,不经意间就认可了一个错误的假设。人类爱欲经济学的拉康式主题,也就是其结构是对无法还原的“缺失”“失败”以及“空虚”的回应,绝对不会自动致使在具体的社会政治变革前景方面表现出不作为或者现代犬儒主义。实际上,情况刚好相反:弗洛伊德所提到的“文明中的不满”(还有拉康追溯到的作为人类欲望固有特性的“文明之前的不满”),恰恰是驱使人类持续改变现状的驱动因素之一。人们之所以不会被动地坚守在一种永远持久的集体生活结构之中,其中一个原因在于某种力比多层面的“不安分”(或许用拉康的话来讲,可以描述成对于社会政治所界定的“剩余享乐”那永不知足的渴望)一直都有希望促使至少一部分人努力去达成对当下状况的种种改变。要是欲望不是以这样的方式运作,如果彻底的满足(也就是充足、绝对的享乐)在幻想或者现实中真的能够得以实现,那么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演变在某个时刻就会突然停止;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来说,真的会出现“历史的终结”。大家不应该被拉康语言的负面意义和暗示所误导——爱欲经济学的功能紊乱对于施加在政治经济上的那些变革力量的存在和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资本主义在压制变革呼声方面不断增强的效力,是因为它劫持了这种永不知足的不安分,将其崇高化地引领到持续增多的、多余的消费需求领域,把欲望中的缺失从一个社会不稳定因素转变成为市场调节消费的引擎(黑格尔在 1821 年就已经预见到的一种阴险的扬弃)。这种操纵性的手段是否能够被扭转,是一个尚未有答案的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马克思指出,“商品恋上了货币”(Marx,1906,p 121)。鉴于齐泽克有关人类现实中恋物癖必要性的精神分析观点,在恋物癖主体(也就是齐泽克所指出的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唯一理智的主体性)、他/她特定的恋物对象(也就是个人所迷恋的特定商品)以及作为所有可能恋物对象的一般媒介的货币(也就是作为普遍的商品恋物癖)之间根深蒂固的三角恋能够被打破吗?或者,这是不是一种三元的疯狂,其相互共生的稳定性(mutual symbiotic stability)将会继续阻抗对破坏的尝试?
列宁所提出的基本唯物主义问题“怎么办?”,其实就相当于对具体实践首要地位的一种基础性且坚定不移的坚守。然而,若要有效地指引干预举措,就必须使其具备更高的针对性、更明晰的背景框架。也就是说,每种特定的情况都应当拥有属于自身的这个问题的版本,以此作为引导连贯的左派行动的疑问。综合迄今为止所阐述的一切,当下必须直接处理的问题——此问题的表述无需理论方面的技术细节、无需智力层面的故弄玄虚、无需晦涩的专业术语——非常简单:怎样才能够消除人们的商品恋物癖?所有反资本主义的实践模式都应当把自身视作对这一棘手难题挑战的回应。搞清楚实现这种消除的办法正是当下务必要完成的事情。各个精神分析学派通常都认为,“性倒错(perversion)”(恋物癖就处于其技术/临床类别之中)尤其难以医治,因为大多数“性倒错者”并不觉得自己是需要被医治的患者;他们一般不会主动寻求治疗。恋物癖者极其不愿意舍弃对其恋物对象的欲望投入。在近期的一篇文章里,齐泽克引用了一个有关资本主义商品恋物癖抵制任何“治愈”(要求放弃对各种恋物对象的依恋)的绝佳政治实例: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拒绝接受国际环境协议(比如规定美国削减过度能源使用),理由是“神圣的美国生活方式”不容妥协或协商放弃(Žižek,2002a,p 328)。这种“生活方式”无非就是一种基于炫耀性消费、基于对大规模生产的消费品的粗俗物质追求和积累(超越了任何合理的界限)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基于商品恋物癖。要是想不出让人们摆脱这种极其昂贵的“奶嘴”的办法——从长远来看,“美国生活方式”由于诸多原因是无法持续的,试图维持它的代价或许会极其高昂——极有可能会致使陷入大规模的灾难。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第二部分:预后——等待神奇疗法
至于那些主张▋▋▋▋因拒绝对人性的“现实主义”观点而难以运作的陈词滥调又如何呢?
更为关键的是,在齐泽克将弗洛伊德 - 拉康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这一方面,于《文明及其不满》的结尾段落里,弗洛伊德在提及“文化超我(cultural super-ego)”怎样忽略本我能够被驯化或者控制的有限程度之时,谈及了自己对于当时刚刚开始的▋▋▋▋政府实验的看法。虽然他承认,改变财产状况非常有可能有利于形成更和谐的社会安排,然而他显然对于仅仅依照他所说的“对人性的理想主义误解”来引导就能成功施行此类计划的具体可行性抱以悲观的态度(SE 21;p 143)。弗洛伊德认为,马克思对主体与城邦之间联系的描绘,对于个体心理能够依照革命目标进行改变的程度怀有过高期望。
人们很难把拉康误认作是左翼激进分子。举个例子,在 1969 年针对参与五月“68 年”起义的学生活动家的公开回应里,拉康对他年轻的“革命者”听众表示不屑。提到他近期提出的“四大话语”理论,拉康告知他们:“你们作为革命者所渴望的是一位主人。你们会拥有一位的。”(Lacan,1990,p127)。这个人对于人类进行彻底变革、实现真正革命性的现实重塑的能力并不抱有乐观态度。作为一名弗洛伊德主义者,拉康坚定地认为,过去总是能够在不断更新的当下环境中悄悄地自我复制,人类的构成和主体性结构存在某些特定特征,不能仅仅凭借意识形态的指令就予以克服。在他 20 世纪 60 年代的研讨会上,拉康特别高兴地反复提及,“革命”存在两种含义(Lacan,1968-1969,3/19/69)。年轻的巴黎激进分子觉得自己正在踏上一条通过颠覆以往价值观来开展革命的道路,而拉康则洋洋自得地提醒他们,革命也有可能相当于围绕一个固定、稳定的点进行旋转(即革命的天体意义)。所以,一场革命实际上或许仅仅是沿着旧轨道多转一圈,是一个让同一个中心维持原位的过程——“la révolution...dans Pemploi qu'il a dans la mécanique céleste,peutvouloir dire retour au départ”(Lacan,1991,p62)。
齐泽克绝非没有察觉到他的拉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张力。在不少场合,他都公开表明拉康依旧深陷在某种保守主义当中,由于对全面向好变革的前景怀有根深蒂固的悲观情绪,只能无奈地接受并不理想的状况(另外可参见Žižek , 2001a ,p 8 ; 2003,p486 ; Kay ,2003 ,p 132)。拉康后期作品里的“圣状(sinthome)”概念(在研讨班二十三中得到阐明)最能够体现这种颇为黯淡的观点:即便精神分析能够治好个体在认知和行为方面的众多症状特征,然而仍然存在无法化解、僵化、对治疗消除的努力毫无反应的愚蠢的享乐核心(参见拉康,1975 - 1976,11/18/75,12/91 75)。这一观点跟弗洛伊德在《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中宣称的情况类似,即分析在碰到“阉割的基石(bedrock of castration)”时就会停滞不前(SE 23,pp 252-253.)。爱欲经济学的惯性确保了变革的参数被限制在特定的界限内,被约束在相对狭窄的可能性以及排列组合的带宽之中。倘若这就是弗洛伊德和拉康历经多年将众多患者的临床观察与为应对这些观察而持续开发复杂理论装置的努力相结合之后得出的观点所具有的特征,那么接受他们想法的任何人又怎么能够避免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怎样,当前状况的某些特征,不管是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必定会永远持续下去?既然依照齐泽克和拉康的看法,个体主体和大他者(作为符号秩序)不可分割地相互交织在一起,难道不必然会得出存在阻碍集体革命改造努力的社会圣状这一结论吗?齐泽克又是如何应对拉康思想的这一方面的?
▋▋▋▋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当代政治想象力关闭这一无可辩驳的现实,使包括齐泽克在内的每一个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的人,都陷入了艰难的境地,等待着某种模糊、未定义的未来事件作为“奇迹”出现,以最终打破看似牢不可破的僵局,打破强大的惯性。齐泽克无疑相信这个“x”终有一天会到来,尽管他受拉康启发对马克思主义的诸多内容持保留意见(他坚持区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诊断描述和作为积极规范性政治计划的▋▋▋▋,将后者斥为“内在的资本主义幻想”另见Žižek,2000c, pp 17-18,19;2001c,pp 18-19;2001d,pp 78-79):
......想象幻想的虚幻充实难道不是掩盖了一个结构性的缺口吗?精神分析难道不主张英勇地接受根本的缺口和/或结构性的不可能性作为欲望的条件吗?这不正是“真实的伦理”——接受结构性不可能性这一真实的伦理吗?然而,拉康的最终目标恰恰相反......“作为不可能的真实”意味着......不可能的事情确实会发生,像爱(或政治革命:“在某些方面,革命是一个奇迹,”列宁在 1921 年说)这样的“奇迹”确实会发生。因此,我们从“不可能发生”过渡到了“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Žižek,2001c,pp 83-84)
对于拉康的某种解读,其倾向于一种坚韧的“实在界的伦理(ethics of the Real)”:在经历“穿越幻想”,并通过拉康精神分析体会“主体性贫困”之后,主体会学着接纳自身的缺失、不满以及不快等等。分析者能够明白机能障碍并非偶然出现的病态,而是爱欲经济学必然的、默认的运作方式。这种领悟促使主体不再对未来的享乐抱有幻想,也就是不再以一种不存在、不可能的标准去衡量实际的快感与痛苦,进而把神经症痛苦的悲情转化为日常挫折的平常(Fink,2002,pp 34-35,36)。然而,齐泽克却拒绝这种解读,原因在于它恰恰支撑了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体所展现出的那种听天由命的悲观主义。它增强了在当前形势的概念限制范围内匆忙放弃任何听起来像乌托邦式事物的倾向。简而言之,它导致了气馁(discouragement)。
在后续的文本内容里,齐泽克批评自己早期的创作陷入了把实在界当作一种康德式本体论的误区,也就是将其视为一个难以触及的维度,它虽然无形,却又无情地干扰了人类现实的其他方面。当谈到《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他的第一本英文著作)时,他宣称其“哲学薄弱点”在于,“它基本上认同了对拉康的一种近似先验的解读,重点是将实在界视作不可能的自在之物;如此一来,它为宣扬失败铺就了道路:即觉得每一个行动最终都会失败,而恰当的伦理态度是勇敢地接纳这种失败”(Žižek,2002b,p xii)。“行动(act)”这个词在此处极其重要,因为它表明了齐泽克所依托的东西,用来避免弗洛伊德-拉康精神分析中常见的那种听天由命的悲观情绪——人们无需将实在界视为一种消极的限制,把一个无法抵达的彼岸围起来,仅仅只是这样去观察和尊重它;人们无需承认主体永远并且最终是过去、本我、符号秩序、驱力、爱欲经济学等功能失调的奴隶,因为与所有这些多重决定因素(overdetermining factors)的彻底决裂是存在可能的。
通过也许过度突显了一个尚未充分发展的拉康概念,齐泽克使自己和资本主义现状维持了一种玩世不恭的距离。依照齐泽克的观点,一个“行动”属于一种干预,依靠重写在给定现实中关于什么是可行的和什么是不可行的规则,“让不可能的事情得以实现”。基于这个前提,他能够同时强调意识形态想象的匮乏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方案的困境——他能够承认取代资本主义的现存方案是“不可能的”——但依旧持续拒绝/拒认对当代令人窒息的封闭状态的这种认知(因为,正如他所宣称的,“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这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了莎拉·凯在她对齐泽克作品的介绍性概述中所着重指出的齐泽克政治思想里“乐观与悲观的惊人融合”,也就是“对现状的悲观,对其可能转变的乐观”(Kay,2003,p154)。而这种“悲观”很可能以一种有症状的方式表明,存在着某种类似于未被承认的恋物癖式分裂的东西。只要在无限期地等待不可能的“行动”——奇迹发生期间,人们继续批判资本主义(恰当地运用纯粹否定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久经考验的资源),人们就可以自由地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非信徒,而把信念留给,比如说,那些“第三条道路”的天真追随者(也许扮演着齐泽克所说的“假设相信的主体”的角色)。难道就没有一种真正的危险,即马克思(作为资本主义的纯粹批判者)和拉康(作为“行动”的思考者)的这种特殊结合本身会在齐泽克自己确切的意义上成为一个理论上的恋物对象,维持着一种“我完全清楚,但仍然......”的立场吗?
正如他的研讨班十五(《精神分析的行动》)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拉康在该年度研讨班的开场会议中着力描绘了“行为(action)”和“行动(act)”之间的差别。前者仅仅是某种自然和/或自动的过程,比如说,身体的运动活动。与之相对的是,后者涉及到超出平常物质事件之类的层面。一个恰当的“行动”有着符号意义的反响:它违背了符号秩序的规则,进而在揭示其缺陷、不一致和脆弱性时,动摇了大他者。行为属于正常“事物进程”的一部分,而“行动”则打乱了支配特定现实的可预测周期,迫使它的监管系统因这种侵入性的爆发而进行转变(Lacan,1967 - 1968,11/15167,11/22/67)。
拉康极力强调的“行动(the Act)”存在一个显著特点,即这种具有破坏性的姿态并非是自我意识经过反思并预先深思熟虑所得出的结果。拉康宣称:“这是行动的一个共通维度,在其瞬间并不包含主体的在场。行动的过渡超出了主体重新找回其在场(以更新后的形式)的范畴,但也仅仅如此罢了。”(Lacan,1967-1968,11/29/67)。这是不是意味着,以一种完全难以解释且神秘的方式,一个行动源于一个非主体性的“无处(nowhere)”,并且唯有通过对这一事件进行追溯性的主体化(subjectivization),才能够谈论任何类型的主体与它存在关联?拉康的行动概念,尽管在概念的独特性和理论的细节方面有所不足,不过包含了两个限制:其一,一个行动无法在既定的符号秩序框架之内被预料和定义,因为当它发生的时候,它会打破这一框架的参数;其二,主体并不会主动地施行一个行动,因为正如拉康所指出的那样,主体性是这样一个事件的被动后续效应(passive after-effect)。
因此,似乎“行动”是一种不可能的、神奇的事件,它无中生有地出现,并降临到那些至少在一开始被动地承受其后续影响的个人身上。事实上,齐泽克本人在多个地方强调了拉康的“行动”理论的这些特征——“我们不能主动决定完成一个行动,行动令行为主体本身感到惊讶”(Žižek, 2001c,p 144;1999c,pp 374-375)。在《易碎的主体》中,这种思路的宗教色彩变得十分明显:
……绝对/无条件的行动确实会发生,但并非以(唯心主义的)由具有纯粹意志且完全有意为之的主体所做出的自我透明姿态的形式发生——相反,它们的发生完全不可预测,是一个神奇的事件,会粉碎我们的生活。用有点可悲的话说,这就是“神圣(divine)”维度在我们生活中的存在方式,而不同的伦理背叛模式恰恰与背叛行动事件(the act-event)的不同方式有关:邪恶的真正根源不是一个像上帝一样行事的有限凡人,而是一个否认神圣奇迹发生并将自己降格为又一个有限凡人的人。(Žižek,1999c,p 376)
从纯粹务实的角度来讲,这样的一种概念存在着传递出一种剥夺权力之信息的可能性:主体的自觉以及意志活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行动事件是以匿名的“它发生了(it happens)”这种模式呈现的,而并非作为有意引导的实践形式所产生的结果。把这种行动观念引入到马克思主义当中,难道不意味着把积极策划革命及其后果的具体政治任务变成了只能无助等待一个抽象且未定义的未来救赎时刻吗?在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开头部分,马克思明确规定:“对宗教的批判的基础在于:人创造了宗教,宗教却没有创造人”(Marx,1964,p 43)。马克思在驳斥黑格尔的政治思想时宣称,精神是一种神智学的幽灵,是一种受意识形态驱动的幻想,掩盖了人类在这一真理的相反面塑造了自身历史的这一事实(也就是存在一种超验的“精神”神奇地支配着人类的命运)。那么,马克思难道不会对拉康-齐泽克的行为提出类似的反对意见吗?因为这有可能重新将异化作为一个模糊和低估战略规划的政治活动的要素。
齐泽克哲学传统主义的高度体现于他对某些即使在后现代狂热浪潮中也极为珍贵且不可抛弃的持久真理的忠诚,也体现于他深信,在精心且深思熟虑地构建起正确的概念框架之前,任何有价值的实践都难以出现。鉴于他貌似支持理论应先于实践这一观点,也就是认为深思熟虑的反思在一定程度上占据首要位置,他对拉康“行动”概念(作为并非由主体引发的无主体事件)的提及就显得尤为奇特。对齐泽克而言,当下首要的“实际(practical)”任务并非某种叛逆的行动展现,因为这说到底不过是一连串无力且不连贯的爆发而已。相反,考虑到在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霸权之下当代社会政治想象力的枯竭,他觉得,如果想要让局面有所好转,首先就必须让思维从当下的束缚当中解放出来。在 2001 年于维也纳进行的一次演讲中,齐泽克指出,鉴于晚期资本主义新的普遍状况,马克思通过直接、具体的行动打破抽象智力沉思的贫瘠封闭这一呼吁(关于费尔巴哈的第十一条提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必须予以颠倒。如今,人们必须抵御为了行动而缩短思考过程的诱惑,因为所有这般匆忙的行动都注定会失败;它们要么无法对资本主义造成破坏,要么在意识形态方面被其同化。
齐泽克觉得,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敢于去冒险,而且无法保证会有任何良好的结果——“真正的唯物主义……恰恰在于接纳这种偶然性,而不暗示存在隐藏意义的前景——这种偶然性的称呼便是意外性”(Žižek, 2002b,p lii)。另外,他再次强调了阿兰·巴迪欧在其 1985 年的著作《我们能思考政治吗?》(Badiou,1985,pp 17-18,31,34)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宣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信念体系借助“极权主义”这个怪物来让这种现代犬儒主义的恋物癖唯物主义丧失合法性——人们通常坚持认为,重新制造如噩梦般的▋▋▋▋▋或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危险,证明了应当避免采取任何偏离西方公认政治信条的激进举措。换句话说,极权主义的幽灵被唤起,目的是压制通过在智力上思考被资本主义民主认定为不被允许的可能性而冒险的需求——“‘极权主义’的概念,远远不是一个有效的理论概念,而是一种权宜之计:它不是促使我们思考……而是免除了我们思考的责任,甚至积极地阻止我们思考”(Žižek,2001a,p 3)。齐泽克接着指出,“当下,提及‘极权主义’威胁维系了一种不成文的思想禁令(禁止思考)”(Žižek,2001a,p 3)。所以,例如“重复列宁”这个表述,并非指另一次尝试发起▋▋▋▋革命时那种荒谬、过时且无效的装腔作势。对齐泽克而言,它广泛地意味着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突破,通过清除认真思考当今统治意识形态强行排除的选项的各类障碍,再次让想象自由民主资本主义的可行替代方案成为可能——“‘列宁’代表着令人信服的自由,能够暂停陈旧的现有[后]意识形态坐标,以及我们生活中那种使人衰弱的思想禁令——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又被准许思考了”(Žižek,2001d,p 51)。
齐泽克把自由民主制借助极权主义威胁的做法,与对作为干预的行动本身更为根本的拒斥关联了起来,原因在于其后果无法被安全地预测。由于担忧可能不会完全依照预期去发展,从而拒绝冒险呈现出破坏的姿态,这成为了抵制变革最为可靠的堡垒——“这种缺乏保障是批评者所无法容忍的;他们期望的是一种不存在风险的行动——并非没有经验方面的风险,而是没有更激进的‘先验风险(transcendental risk)’,也就是说,这种行为不单单会简单地失败,而且还会彻底失败……那些反对‘绝对行动(absolute Act)’的人,实际上是在反对这种行动本身,他们想要的是一种没有实际行动的行动”(Žižek, 2002c,pp 52-153)。拉康有关行动和行为在社会政治承诺方面存在的对立问题在于,人们或许会徒劳地等待一种“没有行为的行动”。行动和行为之间过于清晰明确的区分,使人能够回避核心的问题——“重复列宁”应当意味着在每一个全新的历史背景之下,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提出这个单一的问题——“该怎么办?”基于拉康的理论能够认为,一种行动的出现只能是追溯性地予以确定。一直到已经参与了一系列具体的行动,并且其影响在时间上充分地展现出来,人们才能够评估一种行为是否确实发生了。人们总是在事后才把一种行动认作是这样的(齐泽克本人也承认这一点,见Žižek,2002b,p 222)。所以,正如拉康所坚持的那样,行动并非是由具有自我意识的意志主体在当下引发的事件,因为在此时此地的直接性当中,主体没办法确定或者决定他们的行为最终是否会通过后续历史的裁决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真正行动。主体必须首先投身于行为之中,因为假如没有这些特定的干预,就没有什么能够在事后通过后见之明被把握成为一种行动。虽然一种行动确实不是一种行为(而且远远不是每一种行为都能够或者确实成为一种行动),但是没有行为就不存在行动。一种纯粹行动的政治,一种回避对要执行的行为进行任何具体阐述的政治,属于一种空洞的“没有政治的政治”。这种立场所拒绝的风险并非是“绝对行动”及其可能失败的风险——它存在拒绝积极具体地阐述和执行那些可能最终不会成为行动的行为的风险。齐泽克期望通过推翻某些暗含的意识形态禁令来推动的思考活动,绝对不能忽视应对社会和政治决策的切实细节。等待未定义的行动如奇迹般的弥赛亚式未来的到来这种被动性,是马克思被抛弃的▋▋▋▋政治愿景的唯一可行的替代吗?很快,齐泽克需要解释,在他将马克思主义的肯定规定性议程与其诊断-描述性维度割裂以后,什么填补了剩余的真空。
结论
或许齐泽克近期著作中缺少详尽的政治路线图并非是重大的缺陷。也许,起码就当下而言,最为重要的任务仅仅是批判性斗争所具有的否定性,尽力去治愈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所造成的思想阻塞,进而切实为构思替代当下状况的真实方案开拓出空间。齐泽克所提出的唯物主义的另一种定义为,它等同于接受看似外部的僵局或者障碍的内在固有属性(Žižek,2001d,pp 22-23)(幻想本身被定义成主体内部某种东西的错误外化,也就是内在障碍的虚幻投射,Žižek,2000a,p16)。从这个视角来看,通过学会怎样在当前的限制之外重新思考从而识破意识形态幻想,其自身就有很大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革命实践形式(而不仅仅是消极/批判性的知识反思的一个实例)。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回想一下对于商品恋物癖的分析,货币作为通用交换媒介的社会效力(以及基于此的整个政治经济学)最终仅仅依靠于一种“魔法”,即在交换过程中使用货币的人们对于货币社会效力的信念。由于货币的价值从根本上说可以归结为人们认为它具有所赋予的价值(并且每个人都觉得其他人也这么认为),通过毁掉其基本的金融实质来让资本主义偏离正轨,在一定程度上,就如同消除对于这种实质力量的单纯信念一样简单。资本主义体系的“外部”障碍仅仅在主体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内在”相信它的状况下才存在——资本主义的命脉,即货币,仅仅是对源自同一物质的社会执行力量的信念的恋物癖结晶。然而,资本主义的这一脆弱弱点同时也是其强大力量的来源:它和个体人类欲望的吸血共生,以及晚期资本主义现代犬儒主义者的恋物癖致使他们否认自己实际上对资本主义的信念,这使得人们不太容易仅仅被说服从而停止相信并开始思考(特别是因为,正如齐泽克所说,这些人中的许多人确信自己已经不再相信)。或者,更让人感到不安的可能性是,就算成功地向当今的一些人揭示了他们立场的潜在逻辑,他们的反应方式也许类似于电影《黑客帝国》中犹大式的角色赛弗(赛弗选择接受幻觉的奴役,而不是应对身处“实在界的荒漠”的不适):在生活于资本主义谎言或者与某些令人不快的真相进行斗争之间做出选择时,许多人很有可能会故意决定接受他们完全清楚是虚假的伪现实,一种具有欺骗性的安慰性虚构(“资本主义商品恋物癖还是真相?我选择恋物癖”)。
齐泽克的一则简短评论表明,在一定程度上,他认可马克思主义的这一信念,即资本主义的消亡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对于激进左派的提议属于乌托邦式的指责,最终的回应应当是,在当下,真正的乌托邦是坚信当前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共识能够永远持续下去,而无需进行根本的变革”(Žižek,2001d,p 101)。把乌托邦主义的指责回抛给发出指责的人的这种做法颇具说服力。实际上,任何宣称是“历史终结”化身的制度,都必然会显得是乌托邦式的。鉴于我们对无情的历史进程的了解,认为一种终极的、无法超越的社会政治安排已然到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人们确实应当承认资本主义永远持续下去的可能性极小;它最终必定要让位于其他事物,即便在当前的背景下无法清晰地设想这个“x”。然而,齐泽克自身的理论要求我们对于接受这一观点所产生的后果保持大量的谨慎和保留。在拉康之后,他描述了“以真理的幌子说谎”的策略实例,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现代犬儒主义便是一个关键的例子(在此,现代犬儒地知晓“体制”是空洞的骗局这一真相,却不会在行为上产生真正的改变,也不会决定不再表现得“仿佛”这个大他者具有真正的实质性;Žižek,1999b,pp 61-62)。齐泽克宣称,“意识形态批判的起点必须是充分承认以真理的幌子说谎是很容易的这一事实”(Žižek,1999b,p 61)。正如纯粹消极的、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与对行动奇迹事件的期待相结合,有可能变成一种知识上的迷恋(在意识形态层面,使当下的现实能够忍受),承认资本主义的有限性这一真相也可能带来同样不幸的副作用——人们能够容忍当今的资本主义,是因为知晓它不会永远存续下去;人们可以被动且耐心地等待它终结。在这两种情形下,危险在于齐泽克在对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中所发展的分析本身或许会有助于维持那种现代犬儒式距离,而他对这种距离与当前状况潜在的意识形态共谋也描述得极为出色。
内容版权归原创作者和译者所有。转载本文需经过作者/译者同意,转载时禁止修改原文,并且必须注明来自原创作者/译者,及附上原文链接。
转载、合作、咨询及分析性工作请扫描下方二维码或联系:Jaynight@163.com
相关知识
现代犬儒主义者的恋物:斯拉沃热·齐泽克与信念动力学
恋与制作人李泽言萌宠之约剧情介绍
斯拉兹(斯拉兹拉)
道金斯眼中的世界:对苦难、死亡恐惧与虚无(无意义感)的新应对方案
斯芬克斯猫拉稀给吃什么药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
艾德沃克rfid动物耳标牛羊电子耳标宠物耳环畜牧养殖用品
“相信28”爱沃克证言活动,开启宠物驱虫新时代
萌死人不偿命,国外兴起动物瑜伽热,齐齐带上宠物练瑜伽
138元 爱沃克 德国进口 爱沃克 猫咪体内外驱虫药滴剂预防耳螨跳蚤 大猫用4
网址: 现代犬儒主义者的恋物:斯拉沃热·齐泽克与信念动力学 https://m.mcbbbk.com/newsview120926.html
| 上一篇: 动物模型与评估丨啮齿动物亲社会行 |
下一篇: 互联网时代宠物生活智能化的迫切需 |